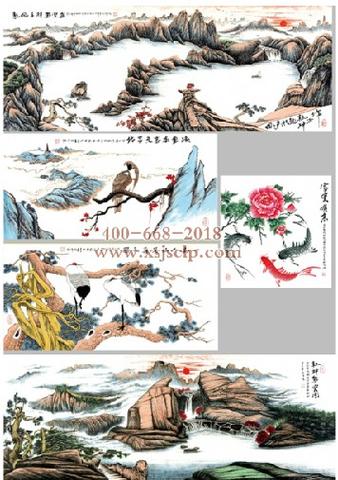此番行脚,心中藏着一个旧念:想看看,从中原一路飘来的道教种子,是如何在这片游牧大地上落地生根,又如何与草原的生命节律彼此交融。翻检旧籍可知,自清代中期起,随着汉族移民北上,山东一带的道教香火便被带入科尔沁。全真、正一两大派别,循着移民的脚步,在农耕与游牧的交界处,缓缓展开一卷别样的文化画轴。
世事如风,宗教如水。水自中原来,入了草原的河道,形态虽变,源头却未曾断绝。此心所系者,正是这条隐伏在草原深处的道教脉络,以及它在当代人心中的余音。

太山宫遗址:民国道观的余音
午后抵通辽科尔沁区时,天色已带一点昏金。按着当地人所指的方向,我寻到了太山宫的旧址。此宫始建于民国六年(1917年),为道教徒吴兴权所建,是通辽早期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。据《360个人图书馆》所记,太山宫曾在当地道教传播中扮演不小的角色。
如今再来觅迹,只见残垣断基,石台隐约,殿宇轮廓若有若无。站在旧基之前,耳边风声猎猎,我却仿佛听见百年前的诵经木鱼、钟磬声声,从岁月深处悠悠传来。
正静看之间,一位年长的牧民从远处牵马而来。见我久站不去,便笑着上前搭话。老人一口汉语裹着浓重的蒙语味道:“你是来看这老庙吧?我小时候就听爷爷说,这里以前香火旺得很,正月里人都来上香祈福。”
他又指着不远处的空地,说当年庙会时,蒙古族、汉族的人都在此处搭棚设市,卖糖饼的、算卦的、唱戏的,一片热闹。老人祖辈为蒙古族,却曾在庙里帮过不少忙,久而久之,也会念几句道教经文。
他笑道:“草原上的汉人和蒙古人,其实很多习俗都混在一起了。我们祭敖包的时候,也拜天地君亲师;过年既敬火神,也听老人讲道家的故事。”一句话,道破了文化勾连的微妙之处。天地间的信仰,本就无高下之分,只是人心对光明的不同表达而已。
扎鲁特天台山:追古华夏的山川回声
山体不算巍峨,却自有一股古拙之气。乱石之中偶见野花,风从谷口穿来,把远处牧场上牛羊的气息也一并带上山来。我心中忽起一念:若真如传说,这里曾是先贤修行之地,那他们当年面朝的天与地,大概也与今日无甚差别。
半山腰处,一位老人正弯腰采药,背后背着旧篓,步伐稳健。彼此问候几句,才知他是当地的道教信众,年年都要上天台山朝拜,顺道采些山中药草。老人向我讲述了一个世代相传的说法:天台山为华夏先祖修行之所,山中藏有通往天地之门的隐秘通道。
他指着一块形态奇异的巨石,神色郑重:“这些石头都是有灵气的,用心去感受,就能听见远古的回声。”我不置可否,只在石旁静坐片刻,让山风从耳畔穿过,让心从喧嚣中退后一步。至于能听见什么回声,那便是各人的缘分了。
草原小观:一位正一道长的守望
李道长为我泡了一壶茶,茶香淡淡,混着些许奶香。他缓缓说道:“道教在草原的传播,其实就是一个慢慢磨合、慢慢融进去的过程。清代中期汉人来的时候,把信仰一并带来。但要扎下根来,就得学会和当地的天、当地的人,相处。”
他指着殿内一角的装饰,说草原上的一些道观,在建筑和陈设上,多少借了蒙古包的意象——圆顶、穹隆,寓意天圆地方。做法事时,有时用马奶酒代替黄酒,用哈达代替黄绢,既不违道教仪轨,又更贴近牧民的生活。
说及当地道教人物,他特意提到了齐大师。据《列表网》资料所载,齐大师是正一派弟子,曾在龙虎山传度奏职,先后学习汉山道人密宗派、元皇派、华光派、圆光派、龙虎玄坛派、玉门派等多派道法,是此地颇有声名的法事大师。李道长感叹道:“他的道法融汇多家,正说明道教向来包容,善于兼收并蓄。”
我听着这些话,心中暗自点头。修行人走南闯北,学的不是花哨手段,而是从多家法门中,悟出一条适合当下众生的路。草原上的道教,也是在这样的碰撞、吸收与转化中,走出自己的样貌。
民俗与斋醮:草原道教的生活气息
一位姓包的蒙古族老人,说起“老鼠娶亲”的风俗时,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他说,正月里,这一带既有道教的祭灶仪式,也有蒙古族祭火的传统,久而久之,一些传说便变成了共同的节日活动。
“正月十六晚上,我们会在屋角点上蜡烛,说是给老鼠娶亲照路。”他半带玩笑地解释,“这习俗有道教禳灾避祸的意思,也有我们蒙古人尊重万物精灵、不随意伤生的道理。”
据《通辽市妇女联合会》资料所记,这类民俗活动中所体现的道教元素,正是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标本。草原道教不只是殿宇中的诵经、醮坛上的科仪,更是渗入了日常生活的节气、故事、禁忌中,和当地人的生活缠绕在一起,难分彼此。
我走出老人家的蒙古包时,天色已晚,远处的灯火在草原上星星点点。我忽然意识到,所谓“信仰”,未必总要高悬于云端,它也可以化身为一根插在屋角的蜡烛,一碗正月里特意留给“老鼠新娘”的碎米。对天、对地、对万物的敬畏,都在其中。

他乡道脉:通辽道人走向远方
李道长说起这位后辈,眼中颇有欣慰:“像他这样从这片草原走出去的道人,其实还有不少。人虽然不在家乡,但心里的那点草原味儿、那点道教传承,是丢不掉的。你看,道教的传播就像蒲公英的种子,随风而去,哪块土地接得住,它就在哪儿扎根。”
蒲公英一落,形态各不相同,却都与原株相连。草原道教走向海边城市、走进大学讲堂,走上网络平台,其实都是同一条道脉在不同空间里的展开。源远流长者,不必拘泥于一山一水。
草原哲思:道教与游牧的心灵相契
道教在科尔沁的发展,其实是一部“文化适应”的实录。全真、正一两派的传入,并非简单地把中原的样式搬到这里,而是在与游牧、农耕双重文化的对话之中,逐渐生成了一种“草原道教”的形态。宫观的布局、器物的用法、仪式的细节,都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,悄悄改换样貌。
更深一层看,这是一种打破二元对立的过程。道教的“天人合一”,与蒙古民族对草原、对山川、对牲畜的敬畏,本是同一条线上的两端;道教强调的“修身养性”,与游牧民族所追求的心灵自由,也有相互呼应之处。
人若执着于“我是你非我”的界限,便容易错过这些暗中的呼应。可只要将心略微放宽,就会发现,不同文明的根部,其实常常扎在同一片“道”的土壤里。
修行与福报:日用之间见真功
我想,无论你此生信奉何种宗教,抑或自称无宗教,都绕不过一个问题:怎样让自己活得更澄明、更有担当。道家与道教所说的“修行”“修心”“积累福报功德”,其实并不是为来世买单,而是让此生的心性更圆满些。
每一次善念刚起时不让它熄灭,每一次恶念欲生时能够收住,每一次伸手帮助他人,每一次对山河草木心怀敬意,这些看似细微的小事,都是在默默积累自己的福德。与其到处求福,不如从当下念头做起。
道教讲“性命双修”:性者,心也;命者,身也。既要在心地上做工夫,也要在身上不荒废。快节奏的当下,多数人忙于谋生,却很少有空回望自己内心。若能在奔波之余,为自己保留一点静下来观照的时间,哪怕是清晨的一炷香,睡前的一次反省,日久天长,境界自会悄然不同。
草原上的道教故事提醒我,文化可以互相成就,信仰可以彼此对话,心灵可以跨越族群而相通。只要愿意放下成见,我们总能在差异中找到共鸣,在多元中看见那条共同的“道”。这“道”,无形无相,却浸润万事万物;它不需鼓噪,却在安静中教化人心。
雨润草原:行脚将尽的余思
我不禁想到,道教在草原上的传播,也像这一场雨。来时远,落地轻,不争形迹,却一点点滋润了这里的生活与信仰。它没有抹去草原原本的颜色,只是在其上叠加了一层新的光泽。
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守旧,而是永在流动中的调整,在不断融合中向前。草原道教的样貌,正是这种动态传承最好的证据。我们每个人,不论自觉与否,都是这条传承链上的一环。说到底,所谓“继往开来”,并不只是史书上的大词,而是我们在日常选择中的一念之差。
行脚终有尽时,求道却无终点。愿有缘读到这些文字的你,在自己的旅途中,也能慢慢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“道”:既不背离本心,又能与这个世界和和气气地相处。若能如此,便已是在默默积累无量福报,成就一份不动摇的内在安宁。
风起草低,云散复聚。此行暂告一段,足迹虽停,心路仍在。
欢迎交流:17333068668